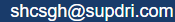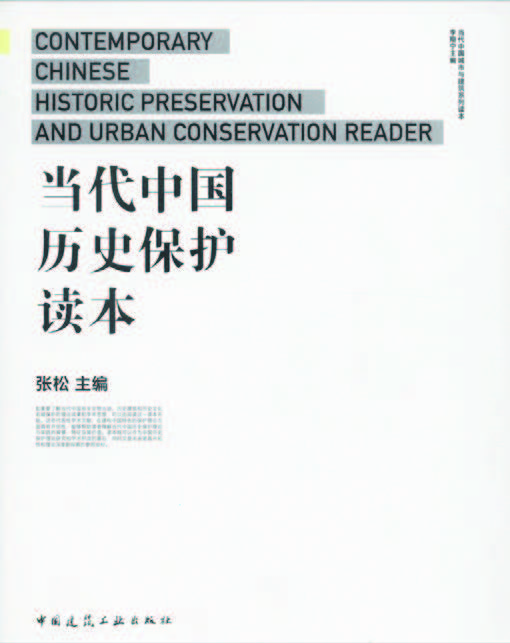
《当代中国历史保护读本》导读
书评作者:童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6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城市设计会议上,面对二战之后的城市边缘扩张与城市中心衰退等现象,众多与会者信心满满地憧憬着,如何通过专业之间的合作,责无旁贷地去为联邦政府十数亿美元的投入计划创造出一种城市新环境、新秩序。而此刻的文化主义者刘易斯•芒福德却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即便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至少大家还可以回去说:为了建立一种物质结构,却以摧毁一个亲密社区生活的社会结构为代价,真是愚蠢至极。”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的若干年前,梁思成在北京则为如何保住北京城墙而绞尽脑汁,因为这一有逆潮流的举动实在难以提供说服力。城墙既不需要用于城防,也不利于交通,而且拆除之后,可以获得地皮,甚至拆下来的城砖也可以移作他用。他总结了当时一种普遍性的态度:“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
梁思成当然不能直接采用芒福德“真是愚蠢至极”的说话方式进行回击,而是“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可以说服的理由:拆除城墙所需的劳动力可以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果实,烧砖窑也可以比拆城砖更为省力,而且环绕的护城河也是天然的水源……
面对着时代狂澜般的现实,既需要应对性的智慧,也需要内部性的反思。针对“自清末以后突来西式建筑之风,不但古物寿命更无保障,连整个城市,都受打击了”的情形,梁思成在另外一种场合做了十分深刻的剖析:“一、在经济力量之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
时至七十年后的今日,经济已经不再凋敝,艺术也相应有所共识,只是梁思成所谓的第三点,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依旧还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对于历史保护的意识,在经过众多坎坷的历程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认同。大多数人都会赞同,一个没有历史建筑和旧城区的城市,就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
每一座城市都必须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保存真实的历史环境,维护鲜明的地方特色,这样的观点说来容易,操作却难。在历史保护领域中,美学、历史和技术层面上的价值冲突在所难免。这并不在于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去做的问题。这种互相冲突的态度和方法必然会在一个正在发展的学科中呈现,而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反过来也会激发在技术、知识方面的探究。
其实这类针对更深层面的讨论也并非始自今日,同一情形也可以追溯到梁思成的另一段史料。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中,当梁思成于三十年后重访河北正定赵州桥时,曾经以同样反讽的方式感慨道,“对于这些历史圣地、千年文物来说,三十年仅似白驹过隙,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变化却是多么大——天翻地覆的30年呀!这些文物建筑在这三十年的前半段遭受到令人痛心的摧残、破坏。但在这三十年的后来——更准确地说,在这三十年的后十年,也和祖国的大地和人民一道,翻了身,获得了新的‘生命’。其中有许多已经更加健康、壮实,而且也显得‘年轻’了”。
梁思成在当时所陈述的“整旧如旧与焕然一新”、“涂脂抹粉与输血打针”、“古为今用与文物保护”等问题,延伸至今日,可以理解为关于历史建筑的复原问题、建筑修复的真实性问题、遗产旅游的原真性问题等,也可以延伸至有关新天地、田子坊等案例的空间经营与人文社会的问题。而这些不同观点一旦付诸实践,则在现实中产生各类效果。复旦大学教授于海就曾经感慨:“保护不仅可以不赔钱,还能赚钱,这一点被所有来参观的市长们都一眼看明白了。当他们乐意通过保护性开发来更新城市时,新天地的模式可能比100个阮仪三更有力地推动城市历史建筑和风貌保护的主张登堂入室。”
由此看来,中国的历史遗产保护问题并非只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扩张大潮的背景所独有,只要涉及时代更迭、空间发展,毁坏与保护就会成为争议性的焦点。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16年底出版的《当代中国历史保护读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视景。
自1982年施行《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以来,中国文化遗产和名城保护实践已经迈过三十多年的历程。无论是在理论提炼还是在工程实践中,围绕名城保护与旧城更新、文物修缮与复古重建、街区保护与商业开发等问题所发生的探讨和争鸣从未停息过。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在实践领域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积累了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管理经验,从而也引导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投入更多的关注。
《当代中国历史保护读本》的主编张松教授,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师从国际保护理事会副主席西村幸夫教授,研究历史遗产保护理论。1997年归国后他一直从事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保护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在城市历史保护领域中的重要人物。
在出版于2010年的《为谁保护城市》一书中,张松教授曾经发出了“救救城市!”的悲壮呼声。“抢救城市,就是抢救人类的居住环境、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就是保护人类的历史档案、文化遗产和共同记忆。简单一句话,抢救城市,就是抢救我们自己。”
这样的呼喊,不仅来自张松教授在自己专业领域中的学识,也来自他在实践中所要面对的现实。他在书中提到曾经在列车上偶遇到的一对上海老夫妻和一位到上海出差的大连人,并引用了他们之间的攀谈:“老夫妻说,哎呀,你们大连近年来变化快呀!大连人也说,哎呀,还是你们上海变化大!老夫妻就说上海是越来越漂亮了,房子越建越多,可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都是造给外国人看的,都是给有钱人去住的。大连人也说道是啊,我们大连也一样……”这类的攀谈很具有典型性,城市变得越来越现代,但城市也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无关。如果说“城市是记忆的艺术”,那么保留着历史的城市则是维系人们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纽带,历史城区的大量丧失,使居民的场所认同感和归属感严重缺失。
城市规划建设,再不能没有历史文化之魂了。
然而,学者的呼吁和媒体的报道,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开发建设中出现的相应问题?如果不从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管理模式、法规制度、宣传教育等各个层面进行认真的反思,恐怕也是难以奏效。这也是张松教授编撰这部读本的主要目的。
《当代中国历史保护读本》所收录的论文主要是基于过去30年来当代中国历史文化保护理论学术领域的历史脉络、现状特征、理论话语和实践经验,精选国内的代表性著述,研究对象范畴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文化遗产理论和文物古迹保护实践,国外或国际遗产保护思潮的影响,以及北京、上海、苏州、绍兴等重要名城的城市保护实践探索等。
《读本》的内容由“经典溯源”、“理论探索”和“学术论争”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早期文物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先驱的遗产保护经典理论,挑选了梁思成和郑振铎两位大家的重要文献,是1949年前后有关历史保护理论的代表性著作;第二部分主要有吴良镛、周干峙、郑孝燮、罗哲文、陈志华、阮仪三等专家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和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上的建设性探索,涉及国际保护理论、文物学基础、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乡土建筑和工业遗产保护等方面,是读本全书的重点;第三部分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包括围绕原真性原则的讨论,以及围绕新天地等实践案例的学术批评等内容。
透过《读本》可以看到,尽管历史保护在制度层面上的设立已有时日,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实践活动中既有相当成功的实践探索,也存在令各方均不满意、甚至是失败的案例。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尽管与历史保护相关的论文每年都有大量发表,但更多集中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建筑保护的案例介绍,理论探索性的文章比重较低,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理论文章相当有限。这也相应反映了编者在梳理中国历史保护在发展线脉时的难度与艰辛。尽管《读本》已经较为完整地汇聚了我国关于历史保护方面的重要成果,同时也相应期待着,在未来会有更多、更好、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理论研究成果诞生。
无论怎样,理论方面的争鸣必将影响到实践方面的导向。一座城市越能深刻地正视、体验它在历史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精神财富,就越能正确地认识自身,就能够以独有的文化品格、地域风情、空间特色而成为它自己。就如张松教授在前言中所引用的法国著名建筑史和历史保护理论家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 Choay)的倡议,“遗产财富在种类上、时间上及地理上三重维度的扩展……或许标志着对当代城市规划的平庸的一种对抗”。